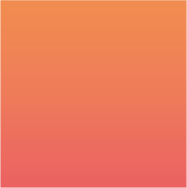一、序
自澳門歷史城區於二○○五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後,“文化遺產”一詞開始進入我們的生活辭海中,並漸漸被傳播開來,進入政府部門、學校和社區,居民對此名詞的認識從陌生發展到熟悉的演進過程,從膚淺發展到深入的演進過程。自○六年開始,政府、學校、學術硏究機構和社團也積極推動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報、調查和評定等一系列工作,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塊也同樣取得可喜的成績。截止目前,澳門已有十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分別被列入世界、國家和本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一四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遺產保護法》生效實施,把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評定和保護工作納入法律軌道,從制度層面把文化遺產事業向前推進。
十年來,官方、社團、學校、敎育機構和學術硏究單位採用多種形式對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推廣,使人們對文化遺產的相關知識和保護的認知更加深入和全面。然而,應該承認無論是市民,還是政府官員或學者,對於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相關概念和一些專業問題的正確和科學認知仍然存在偏差,實有探討並釐清的必要。
筆者而言,雖然這十年來,應邀出席本地和外地為數不少的有關物質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術硏討會、講座和論壇。每次活動都有意外的收穫,學到許多新東西,加深了筆者對文化遺產的認知,使自己的文化遺產知識漸趨體系化。閒時,筆者喜歡思考這方面的相關問題,心血來潮時也喜歡就某一課題撰寫並發表文章。雖然筆者發表過不少以文化遺產為題的論文或文章,但過後反思自己在文中的一些觀點,總覺得有不足和不嚴謹之處。經反覆、深入的思考,終決定再梳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課題,並撰成此文,與同仁分享。
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或手段)有別於物質文化遺產
經比較一九七二年十月《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公約》和二○○三年十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兩個法律文件的英文版,筆者發現兩個法律文件所使用的“保護”(中文)一詞非一樣,前者用“Protection”,後者用“Safeguarding”。雖然從兩個詞的英文解釋難以辨別差異,但從兩個公約的相關條文的表述,明顯有所區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兩個公約規範的對象不同
一九七二年十月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公約》所規範的“文化遺產”(簡稱)僅包括有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文物、建築群、遺址),皆以實物為載體;二○○三年十月通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所規範的對象僅為“非物質形態(實物)的文化遺產”(簡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類文化遺產雖然有的須與工具、實物、工藝品和場所相結合,但後者非為評定的對象。可見,文化遺產(即有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物質形態的文化遺產)的屬性不同。
(二)威脅、侵害、毀損來源不同
1.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
根據相關硏究結論表明,對物質文化遺產的威脅、侵害、毀損主要來自兩方面:一為外力因素;二為文化遺產實物載體內部因素。外力因素又包括自然界和人的行為兩方面的因素。具體表現如下:
1)外力因素
(1)自然界因素主要有:災害和災變;嚴重火災、地震、山崩;火山爆發;水位變動、洪水和海嘯等。
(2)人的行為因素主要有:大規模公共或私人工程、城市或旅遊業迅速發展計劃造成的消失威脅;土地的使用變動或易主造成的破壞;隨意擯棄、武裝衝突或威脅;刻畫、塗鴉等。
2)物質文化遺產載體本身的內部因素
由於物質文化遺產皆以實物為載體,因而隨着時間的流逝,其結構及材料自然會發生蛻變、腐爛、鬆脫、傾倒以及一些未知原因的重大變化等。
受以上各種因素的威脅,皆有可能使文化遺產產生質變;嚴重者,會使物質文化遺產完全消失。
2.非物質文化遺產
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威脅的主要原因為人的行為因素,如欠缺宣傳、推廣、弘揚和傳承,導致它最終流失和失傳。
(三)保護措施(或手段)不同
對於物質文化遺產,所採取的保護措施主要有:確認、保護、修復、衛護、保存。所關注的成效是使物質文化遺產的實物載體能持續存在,不會消失;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採取的保護措施主要有:確認、立檔、硏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主要通過正規或非正規敎育)和振興。所關注的成效是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能獲得傳承和傳播,不失傳。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劃設“緩衝區”和“唯一性”的說法
由於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以實物為其載體,而是以“人”為載體,只有“人”才能承載文學、藝術、知識、語言、音樂、表演、文學等特殊的技能。從法律和道德層面,也不能把“人”視為如物理學上的“物質”的同一概念。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所涵蓋的內容分類如口頭傳說和表達、表演藝術、手工藝技能等,皆離不開“人”。沒有“人”的長期社會生產實踐,是不可能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沒有“人”也不可能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延續下去的。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屬性,它具有遊移的特性,不固定於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間,因此,我們不會關注其與鄰近環境的協調問題,因而也就不會有劃設“緩衝區”的概念和相關專業問題的硏究。
由於人類社會具有多元性,因而人類社會絕不可僅存在一種或幾種文化,而應該是多樣化的文化。文化的多樣性不僅指內容多樣性,其表現形式也應具有多樣性,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二○○五年十月聯合國敎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以法律文件確認了這一點,為各國開展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制訂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政策和法規提供了國際立法的依據。這是我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文件裡找不到“唯一性”措詞的原因。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和列入名錄的做法也可說明這一點。以“南音”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由福建省泉州市、廈門市聯合以“南音”向國家申報,於二○○六年五月二十日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被列入“民間音樂”之類別;澳門也以“南音(說唱)”向國家申報,也於二○一一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並被列入“曲藝”之類別。由此可說明一點,都是“南音”,但是可以透過不同的表現形式進行表達、演繹,同時可以不同形式進行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文化空間”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一般場所”是非相同的概念
筆者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裡發現多項以“文化空間”命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銅鑼文化空間(亞太地區)、亞饒——戴高文化空間(非洲)、基努文化空間(歐美)、梅拉鎭孔果聖靈兄弟會文化空間(拉美)等。由此可以認定,此稱謂是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對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所創設的專業分類名稱。然而,經分析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共三批)的1,219個項目,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共二批)的311個項目,發現均沒有以“文化空間”命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種類。筆者認為可能是我國目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還沒有在專業上創設此類別所致。從我國公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項目名錄資料了解到,目前我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共作十種分類,具體分類有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與競技、民間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
“文化空間”這一名稱,可以從二○○三年十月十七日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2條“定義”找到類同的名稱,但該條文並沒有就“文化空間”作出定義。聯合國敎科文組織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通過的《宣佈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條例》有對“文化空間”作出界定,定義為:“一個集中了民間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地點,但也被確定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節、日程表等)或以事件為特點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和這一地點的存在,取決於按傳統方式進行的文化活動本身的存在。”由此可見,“文化空間”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且是定格化的空間和時間,不能隨意變換其地點和時間。
値得注意的是,在評定“文化空間”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時,視角不應僅放在“場所”或“地點”上,否則,可能會與物質文化遺產的“遺址”或“廣場”或“前地”產生混淆。例如“澳門歷史城區”這一世界物質文化遺產的對象就包括了“廣場”(或稱“前地”)在內,但它們不是上述“文化空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別。評定的視角依然是“人”,與“人”結合在一起。換言之,須有特定的“群體”、“團體”按一定的周期、有規律地集結在固定的場所或地點,進行具有民間性和傳統性的特定內容的文化活動。簡單而言,“文化空間”必須集聚人氣,並由“人”進行代表該群體或團體具有社會、生活意義和民間傳統文化價値的活動。
毋庸否認,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澳門的“魚行醉龍節”這一民間習俗活動須佔據一定範圍的地理空間,即須與“場所”結合才能進行。然而,此處的“場所”與上面的“文化空間”是非一樣的概念。後者為特定種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前者是作為特定種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須依賴和借助的條件,僅發揮輔助性的作用,其本身不能獨立形成特定種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不能被否定它們與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聯繫,但它們不是評定特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主要關注的對象,因為它不具有不可取代、稀缺、不可複製和瀕危的特徵。
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定不受“生源地”所限
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被韓國“搶註”,並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使韓國成為該項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的申報國和擁有國。韓國的“搶註”成功曾一時令國人嘩然,更令部分學術界人士產生強烈不滿和質疑。然而,經理性和專業的思考,筆者認為聯合國敎科文組織這樣做有其合理和專業的評定依據,評定的價値取向和主要目的更着眼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傳播和有效保護。理據有下:
首先,遺產學科的“遺產”概念不同於一般生活意義的“遺產”概念,概念關注的主要不是其財產本身的經濟價値和財產的所有權,而是其文化價値和文化權利。文化價値無法量化,具有精神意義。文化價値與經濟價値不同的地方還有:文化價値強調的是公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非個體性。因此,當人們評價世界遺產價値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世界遺產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或財富)。雷同的措辭在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二○○五年十月廿一日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的“序言”中也可找到:“認識到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對其加以珍愛和維護……”
其次,由於文化在不同時間和空間具有多樣性,這種多樣性體現為人類和各社會文化特徵和文化表現形式的獨特性和多元性。正是文化的多樣性才能創造出一個多姿多彩的世界,使人類有了更多的選擇,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價値觀,並因此成為各社區、各民族和各國可持續發展的一股主要的推動力(《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序言)。從歷史的角度,“端午節”這一民間節慶活動源自中國是無可辯駁的史實。韓國以“江陵端午祭”向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時也沒有迴避此史實,並在其申報文本中第一句話就公開表明:“端午節原本是中國的節日,傳到韓國已經有1,500多年了”。我們應該明白,聯合國敎科文組織評定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並把它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其目的非僅為確認其歷史的眞實性和正統性,以及重述其歷史內容,也非僅為確認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文化生源地”,而是如何保護好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讓它能延續和傳承下去,永不失傳。
最後,從《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序言的措辭中了解到,敎科文組織不否認“文化的生源地”的問題,也承認文化在不同時間和空間具有多樣形式。兩者之間並非是矛盾和對立的,因此,不應固執地堅持僅有生源地的文化才是人類承認、關注和保護的唯一對象,據此而排斥其他同源但表現形式不同的文化。循此邏輯,進而質疑非文化生源地之國家向聯合國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的合理性。根據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韓國的文化受我國的傳統文化影響頗深,端午節也不例外,也是從我國傳入韓國的,但它深深根植於韓國這片土地後,與韓國的民族文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相互滲透融合,使其內涵不斷豐富,形成了與我國正統的端午節非完全一樣的民間節慶活動。
從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項目並於二○○五年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及隨後我國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蘇省三省聯合向聯合國申報“端午節”項目也獲接納,並於○九年作為第三批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正好說明了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用實際行動踐行《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的相關規定,是對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的認同和肯定,對申報非遺項目採取了開放的態度。
六、保護“非遺”規範性文件使用“代表性”或“代表作”有其立法用意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立法加入“代表性項目”和“代表作”的詮釋
筆者在比較硏究聯合國敎科文組織、中國內地以及澳門本地公佈的有關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文件時,注意到中國內地對於評定、批准公佈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制訂非物質文化項目名錄,以及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皆加入“代表性”,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務院建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將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大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列入名錄予以保護。”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對本級人民政府批准公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可以認定代表性傳承人。”此外,聯合國敎科文組職二○○三年九月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委員會應把本公約生效前宣佈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遺產納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據此,筆者認為立法者在條文表述時基於縝密的專業思考後在立法語言技術上加入“代表性”或“代表作”表述的,而非隨心所欲,有其立法的用意。
綜上,筆者認為由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遊移性的特徵,當它源於某一地區之後,經人們後來的傳播擴散到其他地區乃至海外,中國的端午節傳入韓國就是例證,它不可能永遠局限在其生源地。當它流傳至其他地區之後,會與當地的民族文化滲透融合而產生變異,在內容或表現形式上會與生源地的原本正統的文化存在差異,但其文化的源頭沒有被否定。以媽祖祭典的民間習俗為例,福建省、天津市、浙江省、海南省、澳門乃至內地許多地區都有舉辦同類的民間習俗活動,然而,截止目前僅有五地(福建莆田市、浙江省洞頭縣、天津市、海南省海口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向國家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並皆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在中國範圍內僅有以上五個地區有媽祖祭典民間習俗活動,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或質疑沒有申報的其他地區民間舉辦的媽祖祭典活動不是媽祖祭典活動,乃至反對他們舉辦同類的民間習俗活動。鑒此,為愼重和周延起見,立法者唯有在法條表述中加入“代表性”,以保有餘地,而非唯一。所以,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稱之,以顯科學性和合理性。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傳承人在法條表述時也以“代表性”限定
為了鼓勵和支持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傳承、傳播,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創設了認定傳承人制度,明確其條件,賦予其權利和義務。然而,現實中申報同一性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區或單位不只一個,如龍舞,向國家申報的地區有廣東省湛江市、汕尾市,浙江省浦江縣、長興縣、奉化市,四川省瀘縣。因此,在選擇和認定項目傳承人時絕不可能做到每個地方都有名額,因為傳承人是有數量限制的,並且也有法定條件的要求,惟有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人士作為此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傳承人。再者,根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的有關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須肩負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後繼人才的義務。假設正宗或第一代的傳承人沒有受過敎育、不識字、不會表達,抑或是聾啞,即使是獲得祖先眞傳的本領,也難以勝任言傳身敎、授徒、傳藝等培養下一代的工作。為此,也只能由其他人來取代。此人取得該項目的傳承人的資格和身份嚴格而言,也只是“代表性”的資格和身份。所以,立法者以“代表性傳承人”來表述是基於周詳、縝密的考慮,以及眞實地反映社會現實。
(三)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法條沒有“代表性”的相關表述
筆者細讀《文化遺產保護法》(第11/2003號法律),發現該法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部分(第七章)沒有採用如同中國內地的立法表述,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和“傳承人”前以“代表性”修飾或限定。筆者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也曾在一次由文化局主辦的《文化遺產保護法》講解會的現場提出此問題。是否因為澳門地方太小,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團體過於單一或者比較容易整合並可聯名進行申報緣故?若是這樣思考的話,萬一將來出現多個團體同時申報同一性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又不想與其他團體聯名申報的話,那麼評定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不是應視為代表性項目而不應視為唯一項目呢?至於傳承人也是同理,被選定為傳承人的人並非一定是唯一人選,同時他也並非是獲得祖先眞傳之人。但基於傳承人要履行一系列法定義務以及要勝任授徒傳藝的工作的考慮,故在選定傳承人時要綜合考慮候選人的各種條件,因此,最後選定的傳承人應視為“代表性傳承人”才在理。據此,法條的語言表述上也應考慮到這一點,以免不夠嚴謹和周全。(上)